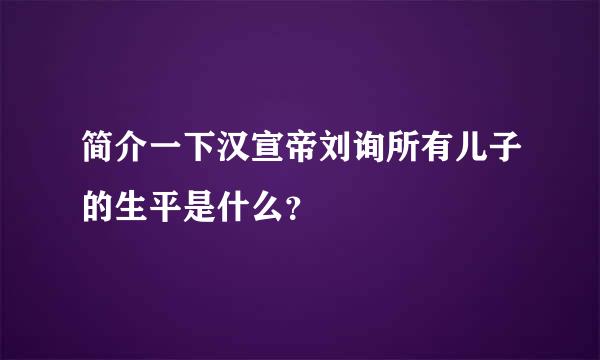影片《阮玲玉》是香港导演关锦鹏在1992年推出的力作,因其视角的独特,套层结构的熟稔运用,触及问题的深锐,故此片一出,便引起众说纷纭。 所谓套层结构,在许多经典影片中都曾经惑人耳目,取得别样意味的效果,如绍拉的《卡门》、还有《法国中尉的女人》等等。套层结构,又称戏中戏,对讲述的故事和正在讲述的人本身形成两个版本(甚或更多,如《阮玲玉》、《暗恋桃花源》等)的交织,人们在观影的同时不断地被打断,被间离,并且常常会因为这种打断而生出反思和客观的理解。这是一份用混淆视听的手段,以期达到不混淆是非的创作者苦心。 《阮玲玉》一片从整体上来分,有两个大的套层:一是阮玲玉生平,一是扮演阮玲玉的演员(张曼玉)在片场,我们称之为关锦鹏摄制组的纪实表现。在前一个套层里,又可以分出三个小的段落——阮玲玉的生活,阮玲玉在摄制组拍戏,(这二者都是张曼玉演绎的阮玲玉)以及阮玲玉电影片段(这是阮玲玉本人)。 描述这样复杂的叙事结构,不是因为对繁复有什么偏好,而是因为在繁复的表面下,读出了演员与饰演演员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里竟有着相同的指认。 在《阮玲玉》中,主题叙事结构当推张曼玉扮演的阮玲玉生平,从她与三个男人(张达民、唐季珊和蔡楚生隐睁)的情感纠葛,与导演们的合作(亦包括蔡楚生),以及阿阮在片场的演出共同构成了一代红伶在人世最后两年的时光旧影。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完成一次重新的剪接:如果没有阮玲玉旧影片和关锦鹏摄制组这两个套层的穿插,那么这该是一部动人悱恻的催泪大片。流畅自然是流畅了,但却也显得平庸。关锦鹏历来以描摹女性细腻内心而著称,有张曼玉出演阿阮,有刘嘉玲出演黎莉莉……她们所身处的甚嚣尘上的香港娱乐界,和她们正在经历的感情变故和97回归御携郑“困境”,凡此种种,可以寓指,缘何不为? 蔡楚生(梁家辉饰演)拍摄《新女性》一场。 阮玲玉在该片中扮演一濒死的“新女性”,规定情境是“新女性”在喊完“我要活!我要活”的台词后,撒手人寰,这时影片结束。 蔡楚生此时一声“收工了”,所有蔡楚生摄制组的人员纷纷离开,惟独阿阮躺在床上没动,她慢慢地把被单蒙住面部,蜷缩在床上哭泣。彼时众人默默,蔡导演走近病床,俯下身来。 我们看到了这一幕,在蔡楚生俯身下来无言以对时,我们接着看到:镜头拉出,先出现蔡楚生剧组的摄影机,再拉出,出现关锦鹏剧组的摄影机,关锦鹏喊道:家辉,你忘了掀开被单看看美姬(张曼玉的英文名字)了! 影片进行到此处,演员和演员所扮演的角色已是水乳交融。在那病榻上久久哭泣的,是“新女性”?是阿阮?还是美姬?! 我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窗户里看我。(卞之琳说的?) 我在台上与霸王把盏言欢,在别人的戏中流自己的眼泪。(张国荣在《霸王别姬》中) 女人演钟馗,打的是自己生活中的鬼!(徐守莉在《人鬼情》中) 呵呵。镇颂 有一条花絮,或能解释美姬在那一瞬间的感同身受,就在接拍《阮玲玉》前夕,她写给导演尔东升的旧日情书被公之于众,正为流言所伤。彼时彼景,与1935年的阮玲玉一般心情! 阮玲玉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并不为关锦鹏所关心。他不会象我们的电影史那样,给这个女人加一个界定,说她是被万恶的旧社会所戕害了的“新女性”。他只想从现代人的眼光去观察和呈现一些过去的人文悲欢。 片中有一妙笔为证: 在阿阮灵堂,导演吴永刚神色肃穆地对镜头说:她问我她是不是一个好人,我说你是一个好人,甚至我认为你是一个太好的好人。 吴永刚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无疑是阮玲玉生平的那个版本,可是在同一个镜头中,吴在前景述说,后景却出现了本来“死了”的“阮玲玉”坐起身来,张曼玉开始补妆,关锦鹏摄制组进入叙事。在这个瞬间,张曼玉从阮玲玉身上分离出来,而吴永刚在关锦鹏面前继续讲述。讲述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而观众对这段反复被打断的讲述(拍了很多条,并且都剪了上去)开始警醒,导演另有他意,打断强调了这一点。 紧接着,黑白画面中,关锦鹏不甘寂寞,他对着镜头说:我不知道当时吴永刚说过这些话没有,这都是我们自己加进去的。 去看一部片子,大多是被那上面的故事骗得五迷三道。很多人习惯那样,本来么,生活已够艰辛,为什么面对银幕,还要思考?!所以,就有更多的片子不用套层,因为他们要满足观众并不过分的要求。但是,电影好在除了娱乐,以及被政治利用以外,还有电影书写者独立思考的功能,通过他们的不媚俗和不妥协,象一切深刻的艺术一样,得以流传。 关锦鹏采取了这种建立(讲述)与破坏(打断)的方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断裂温情的张力,他告诉我们,历史是凭着我们的记忆(阮玲玉旧影片和有关其生平的文字记载)和想象(阮玲玉生平的连贯发展以及对创作者们黑白画面的采访)共同构成的,历史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是它对现实有多大的参照!有谁去追究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史实中并非恋人,他们相差了近百年的岁数,几乎没有相遇的可能。而现世的人们不照样在人民大众口口相传的爱情悲歌中掬一捧辛酸眼泪么?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阮玲玉和蔡楚生似乎并无情感纠葛。这也是为什么关锦鹏借着蔡楚生的名号述说97回归前港人心态的用意,激怒了蔡楚生在大陆的后人。 在《阮玲玉》一片中,有三个男人,闯进她的生活。 唐季珊的见异思迁,张达民的无赖纠缠和蔡楚生的临阵脱逃,是阮玲玉愤然离世的直接动因。人都说流言害死人,所谓“人言可畏”。人言固然可畏,然而最让阮玲玉畏惧的还不是人言,是对男人的彻底绝望!男人把她捧红了(张达民),男人给他锦衣玉食的生活(唐季珊),男人还给她爱情(蔡楚生);可是同样,男人可以毁灭她(张),抛弃她(唐),并且见死不救(蔡)! 选择蔡楚生来寓指阮玲玉生命危机中的稻草,耐人寻味。 对蔡楚生一角的处理,影片没有象表现唐季珊和张达民那样,把蔡也写成一个与阿阮曾相依偎的情人,他们之间,有的是心照不宣的交流和惺惺相惜的默契。 与阮玲玉合作过的导演不少,孙瑜、费穆、吴永刚……可单单只有蔡楚生,关锦鹏不遗余墨地将他与阮玲玉的初识(合影时的迟到)、交往、阮玲玉相邀私奔未果及后来的蔡楚生灵堂昏厥。细心查找,我们会发现在不断地被打断中,阮蔡爱情竟然是一条有头有尾的情节线! 那是归乡,那是温暖的爱情怀抱,那是远避尘世,无限憧憬的未来。 可是,归乡只是一个人的暗自神往,憧憬着的人和憧憬本身还有漫长的路途,甚或,没有通达之路! 蔡楚生让阮玲玉最后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在拍摄《新女性》时,蔡阮有段对话。 蔡蹲在地上说:人有时候是很软弱的,中国有三分之二的人都蹲着,并不是喜欢,是没办法。蹲着受侮辱,蹲着等救星。 阮玲玉说:还蹲着休息:) 蔡楚生看着阿阮:不要高高在上,蹲下来让我看。 于是,阿阮蹲了下来。 就是这样一个不高高在上,总是蹲着看世界的蔡导演,拍摄着三十年代的进步影片,深受阿阮信赖,在那个充满伤感的聚会上,阮玲玉吻他最深。然而,在阮玲玉身陷困境,求助于他时,他没有援手。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忘记这个段落: 阮玲玉走进餐厅,蔡楚生已在桌旁等候多时。阿阮迟疑求助,蔡楚生顾左右而言他。阿阮下意识地捏起蔡弹落在桌上的烟灰,吃进嘴里…… 那近乎自虐的行为使无路可走的名伶绝望毕现。 画面处理更是独具匠心:蔡阮二人始终不在同一画框中同时出现。开头,阿阮在画面左侧露身,急切之情在压抑中流露出来,而此刻的蔡导演根本不在画中,他那轻描淡写,闪烁其辞的画外音令人齿冷,整个背景是一面白墙,从门外射进来的一缕阳光将他的身影映照在墙上。那是在场的缺席者,是个逃兵。(为阮玲玉所信任的,不过是下午阳光里的一个影子而已)蔡楚生在段落的结尾入画,为的是拒绝与阮玲玉私奔香港,此时,阿阮已悄然退出画框,起身离去,只留下赤色的导演独坐。 在阮玲玉的灵堂里,蔡楚生是唯一没有发言的导演,他在人群的后面怅然若失,最终倒了下去。这个蹲下来看世界的进步人士,在爱情面前退步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帽子扣在蔡楚生头上? 众所周知,蔡楚生是中国三十年代著名的左翼导演,他的身上可以折射出一代人民电影工作者的影子,把他处理成一个不负责任、有些怯懦的人物,实在是导演关锦鹏们忧虑心态的外化表现。拍摄《阮玲玉》在1992年,而5年之后,香港即将回归。受英国殖民统治一百年的香港人在回归面前,欢欣鼓舞的人并不多,心存忧虑的很不少。在那一段时期,如何面对97,成了香港影视传媒极为敏感和关注的焦点。有评论者据此提及徐克们拍摄的《东方不败》系列影片,说香港人实际上有一种“东方不败”式的不男不女的自我寓指。殖民地的长期精神阉割,很难让他们对回归有充分的归属感。那代表了进步的电影界前辈,能给前路茫茫的优伶一个温情的怀抱吗?